近日,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等单位共同举办好思汇:“气候传播2025”讨论会。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滕飞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气候传播与风险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曾繁旭教授,澎湃新闻高级记者刁凡超分别做主题发言,并与观众就气候变化领域传播的舆论事件、科学原理、实践经验进行了交流。活动由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传播经理吕雅宁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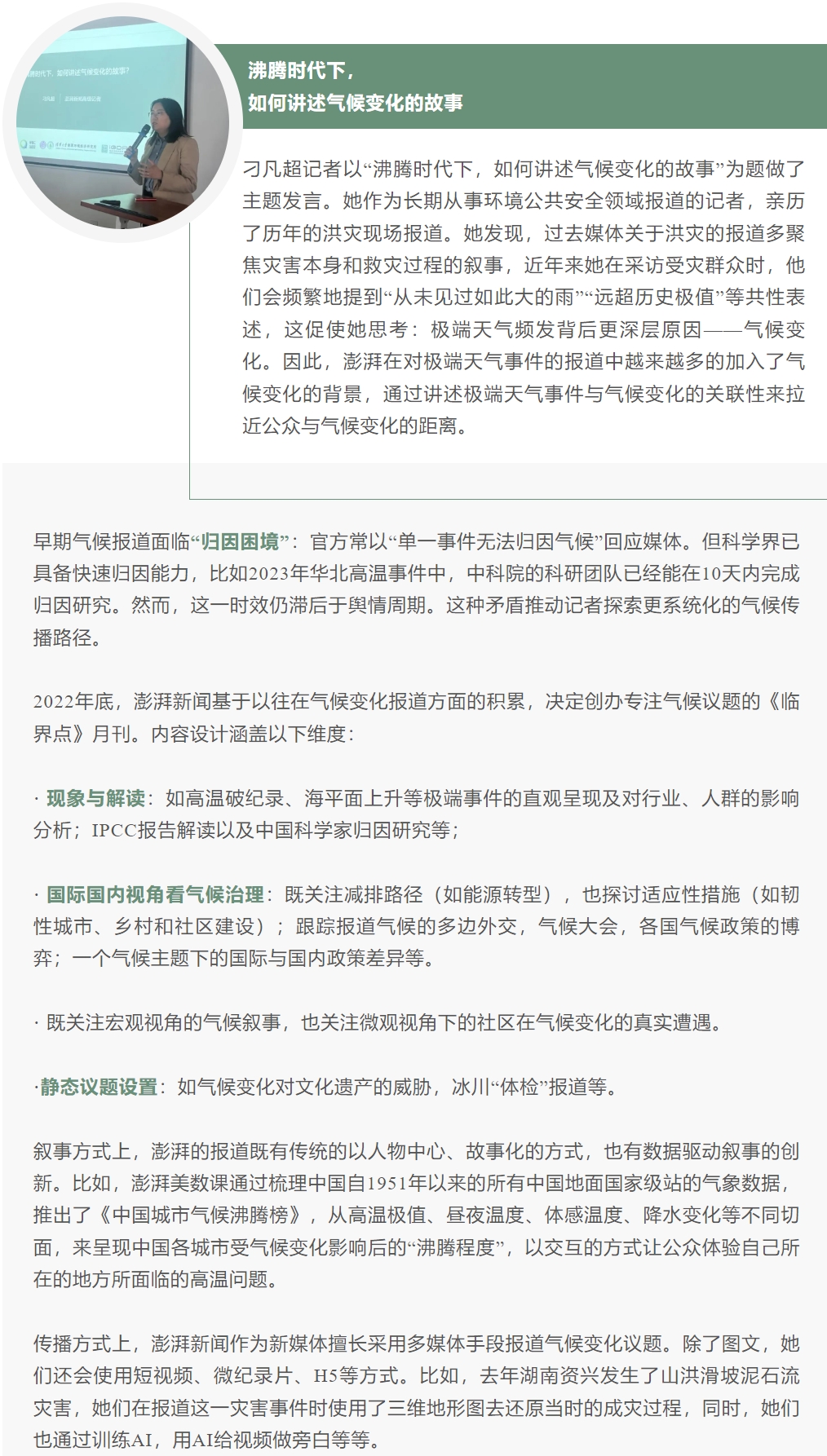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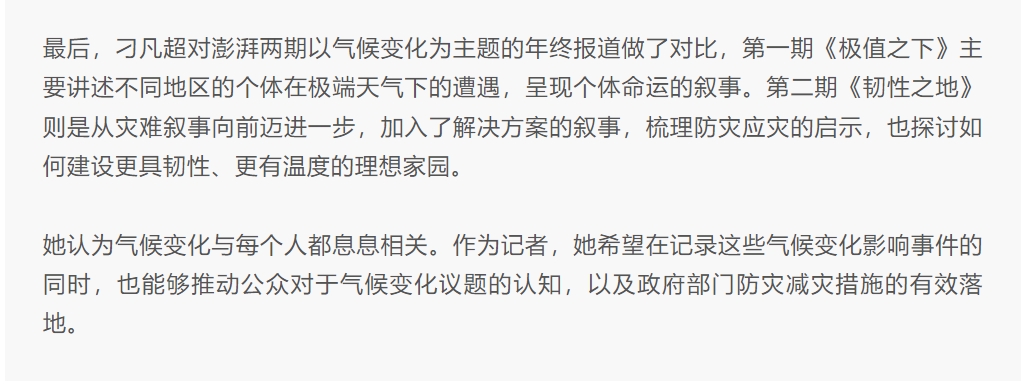

吕雅宁:气候变化议题常常被认为是“远方的哭声”,尤其是对于那些发生在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地区的气候事件。公众可能更关注经济、就业、健康、教育等直接影响生活的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林方舟:在我看来,气候问题不只是“远方的哭声”,更是“近处的呐喊”,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大众对气候变化议题的认知仍待提升。我之前写过一篇有关气候桌游的文章,我发现气候主题桌游虽然有趣且设计精良,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仍不如经济类或历史文化类桌游。这反映出普通大众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我认为媒体有责任让人们意识到气候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引导公众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行方法。
崔绮雯:公众更关注与健康和经济相关的环境议题,这是人之常情。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的气候报道,作者通常会考虑目标受众,尤其是受气候问题直接影响的群体。虽然一些气候问题看似遥远,但实际与本地密切相关,因此报道需要从在地角度出发。虽然复杂的气候概念(如IPCC、1.5度目标)对非专业人士较难解释,但将其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如雾霾影响)连接起来,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吕雅宁:气候报道往往有“危机感”和“希望感”两种叙事风格,大家如何看待两种叙事风格的差别?以及如何平衡二者,既让公众意识到气候问题的严重性,又能激励公众行动?
崔绮雯:对话地球更倾向于做基于解决方案的报道,尤其是针对英文读者,他们大多是关注气候问题的企业人士或消费者。英文气候报道中,关于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已经说得太多,读者容易产生厌倦和焦虑感。因此,我们希望更多地展示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比如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和行动。
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案例和方法,比如产业地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居民如何参与等。此外,通过艺术或其他表达方式缓解气候焦虑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林方舟:目前气候传播中,危机叙事和解决方案的叙事风格及其受众存在割裂。危机感的叙事多聚焦于个体故事,面向普通读者;而解决方案的叙事则多围绕政策和自上而下的策略,如可再生能源投资和政策规划,缺乏对普通人行动的回应。因此,普通人虽然愿意参与讨论,但常感到自己的减排努力无法与大企业的排放量相比。
媒体可以根据受众特点进行平衡,例如在讲述气候危机的个体故事时,可以同步引入普通人能够参与的解决方案。
吕雅宁:以年轻群体为例,特别是Z世代,这类人群在接受气候领域的信息时,有哪些差异性特点、行为偏好?
武昕竺:我认为年轻群体对信息的情绪价值和互动性要求较高,传统的硬核气候知识往往难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因此,不仅要选择年轻人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还要将晦涩的气候知识转化为有趣、易懂的内容。
我还观察到,Z世代虽然关注气候危机,但常感到无力改变。比如,2024年梅州水灾等灾害频发,公众关注度却在下降。我曾经在一个关注灾害救援响应的社群(卓明信援学习社群),发现实际上有很多普通人可以参与的灾害干预措施,但是并未被广泛认知。因此,需要为年轻人提供更多行动路径,帮助他们从关注者变为行动者。
吕雅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气候传播工作中也有很多新的工具。如何利用AI、数据可视化、短视频、新型社交媒体等,突破传统传播壁垒,扩大气候传播工作的影响力?
武昕竺:我在观察大众舆论中发现,年轻人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有一种“失权感”,他们与父辈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更多依赖网络建立社交关系,现实中缺乏改变的机会。小红书等平台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们营造了社群感,让人们可以一起吐槽和交流。因此我认为可以通过建立更紧密的气候社群,让人们从抱怨转变为积极探讨和行动,从而在新媒体时代更好地推动气候传播。
林方舟:《南方周末》作为传统媒体,以文字报道为主,同时也在尝试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呈现气候内容。此外,还通过做智库、发布研究报告等方式,针对企业漂绿行为进行公众监督,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崔绮雯:对话地球虽然以文字报道为主,但会结合多媒体设计增强表现力。例如,我们曾将非洲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农户故事制作成连环画形式的线上展览馆,类似H5网页,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个人则尝试用AI进行气候主题的小说和虚构创意写作,探索新的传播形式,虽然目前还处于业余尝试阶段,但觉得这种形式很适合社交媒体传播。
吕雅宁:“对话地球”作为一家具备国际视角的气候传播机构,在您的过往报道经验中,中国的哪些气候行动更容易引起国际关注?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崔绮雯:海外读者对中国工业转型和新技术应用非常感兴趣,但需要合适的专家来解读相关内容。同时,海外读者渴望寻找新的叙事方式来理解中国。因此,我们致力于通过政策解读,让普通读者理解政策的影响和含义。
此外,海外读者对中国本地社区的气候行动和地方特色(如养蜂者、川茶、云南咖啡等具体议题)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浓厚兴趣,但这些内容在国际媒体上鲜有报道。挖掘这些在地故事和行动,不仅有助于打破国际媒体的刻板印象,也能为海外读者提供更真实、多元的中国气候行动视角。
吕雅宁:在进行传播工作或选题策划时,每个主题所涉及的相关方和学科领域往往差异很大,大家是否感受到这种挑战?如果是的话,你们是如何应对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的?
林方舟:气候变化传播面临内容和受众多样性的挑战。传统上,气候变化被视为国际谈判议题,如今已扩展到经济、能源转型、交通转型等多个领域,并涉及不同社群和人群的影响。这种多样性要求媒体记者快速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并向专业人士请教。
为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团队尝试“去气候变化标签化”的传播策略,避免直接提及“气候变化”,而是通过生动的故事和接地气的语言,将与普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如遇极端天气户外活动取消、高温天气、菜价上涨等)呈现出来,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理解这些现象与气候异常的关联。这种策略既能避免受众抵触,又能有效传播气候变化的影响。
武昕竺:我会根据年轻人的兴趣快速进行桌面研究来了解相关话题。我从去年开始关注极端灾害议题,发现公众对灾害失去热情是因为缺乏相关知识。我正在筹划一个关于中国如何进行防灾减灾行动的选题,并试图通过可视化手段展现。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得到专业人士的关注并建立联系。
崔绮雯:我们通过在地化的方式与不同群体紧密合作来获取报道线索和多元视角,包括跨领域、跨人群沟通,与民间组织、工会等保持日常紧密联系等。例如,关于舟山“幽灵渔具”的报道来自当地NGO组织的线索。我们还通过与“和气行动”等组织合作,了解到社区气候风险识别工具等信息。
本文转发自:iGDP 公众号